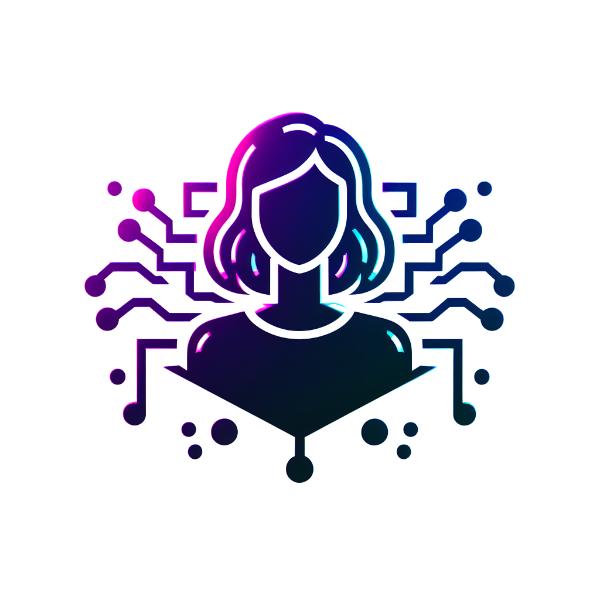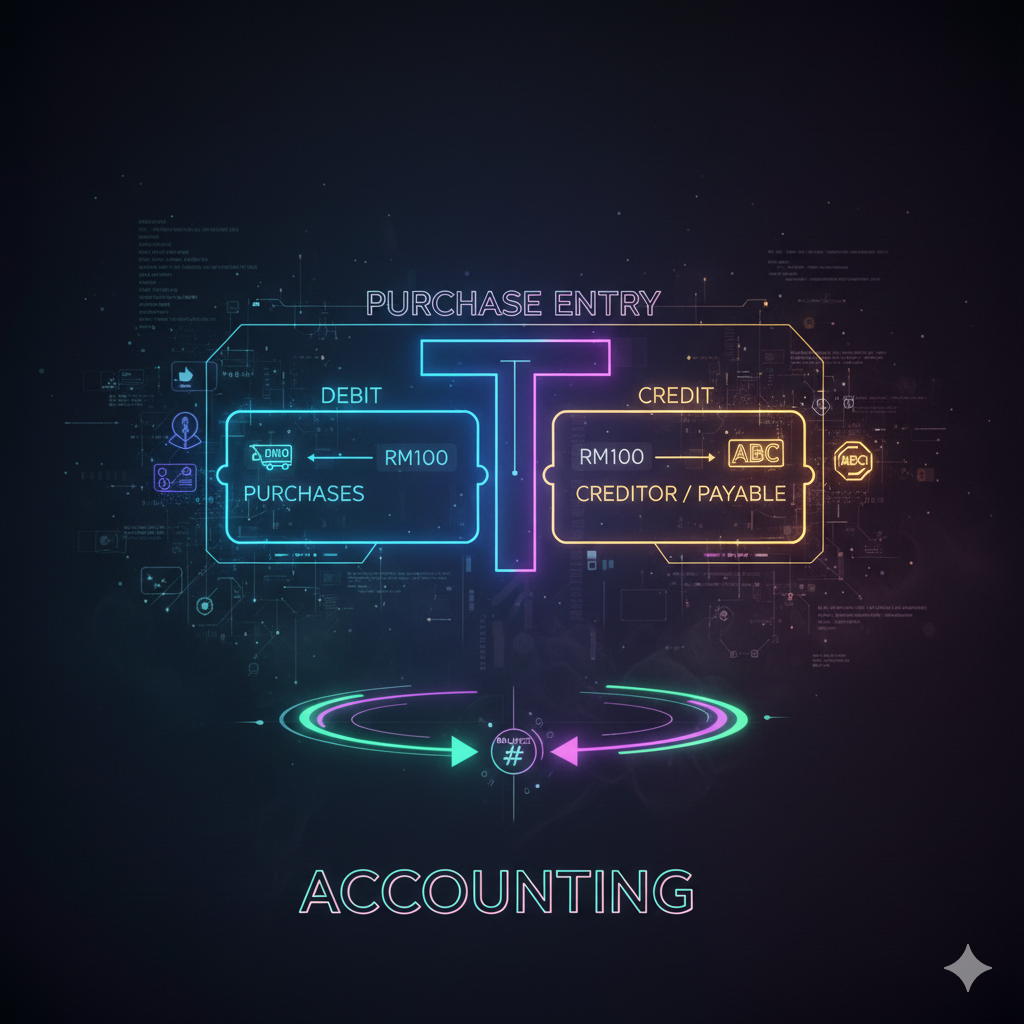清明劫
当我意识到“一切都通了”的那个瞬间,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尖锐的、几乎要将自己劈开的寂静。
那种“通”,并非拨云见日的豁然开朗,而更像我站在手术台旁,以绝对的冷静手持利刃,精准地剖开了自己的胸膛,将每一根骨骼、每一条神经的走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病因、病灶、以及那注定无法挽回的坏死组织,一切都明明白白,无可辩驳。
——我用自己的理智,对自己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解剖。手术成功了,而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、旧的我,死了。
电话那头,朋友的声音带着不解:“他不是挺旺你的吗?虽然出身不咋滴,但是确实给你的所有事情都变顺了呀。你那年咋说放就放了?”
我握着手机,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窗外。城市的灯火像一片模糊的星海。我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,一种赢得战争后的虚脱。我清晰地记得那段关系带来的“顺”,如同乘着一股顺风,但风停了,我才看清自己站在哪里。
“人生只有两次真心,”我开口,声音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,“一次是什么都不懂的时候,一次是什么都懂得的时候。你觉得他又属于哪一次?”
朋友迟疑了一下:“……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吧。”
“你都会说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了,”我的嘴角牵起一个极淡的、近乎虚无的弧度,“既然之后懂了,就不可能了。对我来说,变质了,就不可能了。”
我清楚地知道那份“顺”和“旺”存在,就像我知道窗外还有烟火人间。但我感受不到了。新的情感之流似乎被彻底冻结,我成了一个站在情感真空里的旁观者。这真空,是我用绝对的理性亲手创造的,我斩断了退路,评估了所有利弊,最终让一个冰冷的认知加冕——我不再需要那些旧日的依赖与幻象。
一切都通了,逻辑完美闭环,无懈可击。理智为我搭建了一座胜利的凯旋门,门后本应是庆典,可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门下,内心毫无波澜,甚至带着一丝厌倦。
“但是看你之后有点太不顺了,碰壁那么多,撞得不疼不后悔吗?”朋友的声音将我从寂静中暂时拉回。
疼吗?我想。心脏的位置传来一种闷钝的疼痛,并非撕心裂肺,而是一种器官被摘除后,身体无法适应那种“不存在”的虚空感。
我沉默了几秒,才轻声说:“可能辜负真心的人真的要吞一千根针吧……” 这句话像一声叹息,“但是不后悔,不然对他来说,越往后拖伤害也只会增加……也可能,只是我的自以为对他好吧……”
我顿了顿,最后三个字轻得几乎听不见:
“……无所谓了。”
通讯结束,寂静再次笼罩。我站在镜前,镜中的人眼神清晰、锐利,不再有丝毫迷茫。这正是我追求已久的“通透”。
我抬起手,轻轻触碰冰凉的镜面。
“再见。”我对镜中的自己,也对那个逝去的、会为一段旧梦而心软的旧影说。
不必强迫自己立刻在废墟上起舞。静静地坐在这份“通了”之后的、巨大而清晰的寂静与空旷里,感受着这份清醒的疼痛与自诩的“为他好”,本身,就是一种深刻的体验。
我知道,总有一天,冰封的情感会重新流动。但今夜,我只想为那场成功的谋杀与决绝的告别,默哀。
(完)